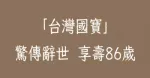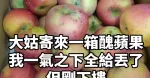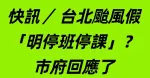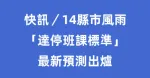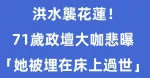3/6
下一頁
為啥打敗仗叫「敗北」,請人吃飯叫「做東」,死叫「歸西」?

3/6
元代筆記小說里,「做東」已用於請客場合。
《水滸傳》里,柴進請晁蓋,「說道:『某家做個東道,請哥哥們敘敘舊。』」——直接用「做東道」表達請客。
而「東道主」則更早,出自《左傳·僖公三十三年》:晉侯款待秦伯,「曰:『寡人之東道主也』」。
那是國與國之間的招待,從此「東道」不再只是方向,而是責任,是身份。
這就是為什麼做東不能隨便說,那不是主動請客,是承擔身份義務,做東的人,要出面、出錢、出席,還得出主意。
你若把飯局當成應酬,他卻是在遵禮。
現代人圖方便、圖平等,覺得「坐哪都一樣」,但飯局上誰坐主位,誰點菜,誰買單,大多數時候早已按古法安排得清清楚楚。
只是少人知道,那是兩千年前定下的「東為主」在發力。
細節決定認知,認知決定結構,連請客這件小事,都逃不出「方向=權力」的邏輯。
歸西,是信仰驅動的語言選擇
一個詞能活千年,不是它好聽,而是它剛好,遮住人最不想直視的恐懼。
「歸西」就是這種詞,第一次在訃告中看到這兩個字,莫名其妙:死了,就不能直接說死?非得說「歸西」?歸哪裡?為什麼是西?
要回答這問題,得看佛經。
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里有一句: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,有世界名曰極樂。」
極樂世界在西方,這句話後來成了,整部佛教喪葬文化的軸心。
西方不是地理意義的方位,是靈魂往生之地,是死者的歸宿。
唐代以後,佛教盛行,「西方極樂」就逐漸和「死亡」綁定。
死不再是「終」,而是「去另一個地方」,語言開始變得溫和,不說「死了」,說「西去了」「歸西了」「往生了」。
宋人筆記《夢粱錄》中寫到一位官員去世:「公已西歸,親朋皆赴喪。」這裡已經非常自然地用「西歸」代替「身亡」。
《水滸傳》里,柴進請晁蓋,「說道:『某家做個東道,請哥哥們敘敘舊。』」——直接用「做東道」表達請客。
而「東道主」則更早,出自《左傳·僖公三十三年》:晉侯款待秦伯,「曰:『寡人之東道主也』」。
那是國與國之間的招待,從此「東道」不再只是方向,而是責任,是身份。
這就是為什麼做東不能隨便說,那不是主動請客,是承擔身份義務,做東的人,要出面、出錢、出席,還得出主意。
你若把飯局當成應酬,他卻是在遵禮。
現代人圖方便、圖平等,覺得「坐哪都一樣」,但飯局上誰坐主位,誰點菜,誰買單,大多數時候早已按古法安排得清清楚楚。
只是少人知道,那是兩千年前定下的「東為主」在發力。
細節決定認知,認知決定結構,連請客這件小事,都逃不出「方向=權力」的邏輯。
歸西,是信仰驅動的語言選擇
一個詞能活千年,不是它好聽,而是它剛好,遮住人最不想直視的恐懼。
「歸西」就是這種詞,第一次在訃告中看到這兩個字,莫名其妙:死了,就不能直接說死?非得說「歸西」?歸哪裡?為什麼是西?
要回答這問題,得看佛經。
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里有一句: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,有世界名曰極樂。」
極樂世界在西方,這句話後來成了,整部佛教喪葬文化的軸心。
西方不是地理意義的方位,是靈魂往生之地,是死者的歸宿。
唐代以後,佛教盛行,「西方極樂」就逐漸和「死亡」綁定。
死不再是「終」,而是「去另一個地方」,語言開始變得溫和,不說「死了」,說「西去了」「歸西了」「往生了」。
宋人筆記《夢粱錄》中寫到一位官員去世:「公已西歸,親朋皆赴喪。」這裡已經非常自然地用「西歸」代替「身亡」。
 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