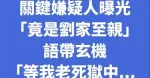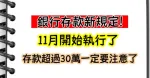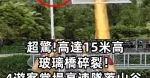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他當了33天皇帝,卻被罵了900年,死後老家鄉親都拒絕他入葬祖墳

3/3
張邦昌率領汴梁舊臣,向趙構稱賀。他親手將玉璽奉上,將汴梁城的艱難維持,以及自己所做的一切,「坦白」地向新皇帝趙構彙報。
趙構見到張邦昌,心情是非常複雜的。
一方面,他知道張邦昌的「傀儡皇帝」生涯,確實是金人逼迫的結果;另一方面,張邦昌主動歸政、奉上玉璽,為南宋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沒有張邦昌在汴梁的「代理」,京城可能早就被徹底洗劫一空,趙構的繼位也不會如此順利。
趙構不是一個傻瓜,他懂得其中的利害關係。 如果他立刻殺了張邦昌,不僅顯得自己「不仁不義」,更重要的是,會向那些曾經在金人威逼下「委曲求全」的舊臣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:投降或屈從金人者,一律殺無赦。
這只會讓更多的人,徹底倒向金人。
因此,趙構做出了一個「政治上最正確」的決定:赦免張邦昌。他封張邦昌為同安郡王,表面上給予了極高的禮遇。
張邦昌暫時逃過了一劫,他的心頭大石似乎落了下來。他以為自己的「曲線救國」策略成功了,用33天的屈辱,換來了自己的生路,也換來了南宋的喘息。
然而,他低估了「文人士大夫」的道德標準,也低估了「主戰派」的政治力量。
李綱的怒火,一個繞不過的道德困境
張邦昌雖然得到了皇帝趙構的赦免,但朝堂上的「主戰派」,卻絕不答應。其中,最堅決、最憤怒的人,就是當時力主抗金的宰相李綱。
在李綱等一眾「鐵骨錚錚」的士大夫眼中,「叛國」就是死罪,無論你有什麼苦衷,無論你做了什麼貢獻,你登基的那一刻,就是對趙宋皇室最大的背叛和羞辱!
「名節」重於泰山,生死輕於鴻毛。 這是宋朝文人的普遍價值觀。在他們看來,張邦昌應該像那些忠烈之士一樣,寧死不屈,以身殉國,而不是為了苟活,去當金人的「傀儡」。
李綱堅決上奏,要求嚴懲張邦昌。
他的理由非常簡單而有力:張邦昌的「僭越稱帝」,是國家之恥,如果不對其嚴懲,如何能震懾天下叛臣?如何能挽救趙宋王朝的衰落形象?
李綱的堅持,代表了主流的道德和政治正確。趙構雖然想保張邦昌,但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和士大夫群體的憤怒,他開始動搖。
更要命的是,有人告發張邦昌在當「皇帝」期間,玷污了皇宮裡的宮人。這個指控,讓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張邦昌,徹底失去了道德上的支持。一個為保全性命而屈從於敵人的大臣,竟然還做出玷污宮人的醜事,這在道德上是絕對無法被接受的。
在李綱的堅持和輿論的壓力下,趙構最終無法抗衡。他被迫對張邦昌進行「處理」。建炎元年六月(1127年7月),張邦昌被貶往潭州(今湖南長沙)「安置」,美其名曰是「避禍」,實際上是流放。
張邦昌的命運,被政治和道德的雙重絞索,越勒越緊。 他那33天的「皇帝」經歷,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一個永遠無法洗清的污點。他雖然人在潭州,但心知肚明,自己的生命,已經進入了倒計時。
賜死潭州,一生的掙扎化為一聲嘆息
被貶到潭州之後,張邦昌的日子,過得異常屈辱和艱難。他的行動受到嚴格監視,一舉一動都要向朝廷報告。
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,很快就來了。
金人得知張邦昌被貶的消息後,非常不滿。他們威脅南宋朝廷,稱「如果張邦昌被廢,我們就要再次南侵!」
金人的這番話,無疑是將張邦昌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。對於趙構來說,張邦昌的「政治價值」已經徹底消失,反而成了「招惹金人的麻煩」。
一個活著的張邦昌,是金人南侵的藉口;一個死去的張邦昌,才能平息朝堂的怒火和金人的藉口。
建炎元年九月,宋高宗趙構下詔,將張邦昌賜死。
接到詔書的張邦昌,讀罷之後,「徘徊退避,不忍自盡」。他是一個文人,雖然經歷了人生的巨大起落,但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,他仍然心有不甘。
他一生都在掙扎,在忠君與保城之間掙扎,在道德與苟活之間掙扎。最終,他所有的掙扎,都化為了一聲嘆息。
在執行官的逼迫下,張邦昌最終登上了潭州城內天寧寺的平楚樓,自縊身亡。
這個做了33天皇帝的男人,用自己的死,為南宋的建立獻出了最後的「祭品」。 他的死,既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,也是宋朝文人「名節」至上價值觀的犧牲品。
他死後,趙構為了安撫他身後的親人,也為了顯示自己的「仁慈」,曾下詔禮尊張邦昌,讓他的子孫親屬獲得錄用。但這並不能改變張邦昌在歷史上的悲劇性地位。
死後千年罵名,老家祖墳都不要他
張邦昌死了,但他的罵名,才剛剛開始。
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歲月里,「張邦昌」這個名字,成了「漢奸」、「賣國賊」的代名詞。他是南宋人心中最痛的恥辱,是「靖康之恥」中最鮮活的「叛國者」形象。
宋朝的史官們,秉承著「名節」至上的原則,將張邦昌的所作所為,毫不留情地釘在了史書上。他的一切苦衷和努力,都被那33天的「皇帝」經歷所掩蓋。
後世的文學作品、戲曲小說,更是對張邦昌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醜化。 在民間故事裡,他被塑造成一個貪生怕死、趨炎附勢的小人。
這一罵,就是整整九百年。 直到今天,只要提到靖康之變和偽楚政權,張邦昌的名字,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「反面教材」。
更讓人唏噓的是,張邦昌死後,連回老家安葬都成了一種奢望。
張邦昌是河北東路永靜軍東光縣(今河北滄州)人。當他的家人打算將他的遺骸運回老家,安葬進張氏祖墳時,遭到了老家鄉親們和族人的強烈拒絕!
「一個曾僭越稱帝、辜負大宋的叛臣,沒資格入葬我們張氏祖墳!」 鄉親們義憤填膺,認為讓張邦昌入土為安,是對祖宗的「大不敬」。
這是何等的悲哀和屈辱! 張邦昌一輩子都在為自己的名節掙扎,到頭來,不僅自己被賜死,連死後都落得「無家可歸,祖墳不容」的下場。
他用33天的皇帝生涯,換來了一個家族長達數百年的恥辱。 他本想「曲線救國」,卻最終成了「兩邊不討好」的千古罪人。
張邦昌的「不得不」
回過頭來看張邦昌的一生,我們不能簡單地用「忠臣」或「奸賊」來給他定性。他的故事,是一個時代悲劇下的個人悲劇。
張邦昌的「不得不」,反映了宋朝文官在民族大義和個人存亡之間的巨大困境。他沒有武將的英勇和決絕,也沒有士大夫的堅貞和赴死,他只是一個渴望和平、想要保全城池的文人宰相。
在金人兵臨城下,宋徽宗、宋欽宗束手無策的情況下,誰來保住這座城?誰來為城中的百姓爭取一線生機?
張邦昌用自己的名節和性命,為汴梁城換取了暫時的安寧。 他在位期間,沒有主動殘害宋朝宗室,沒有大肆屠殺百姓,反而做了「歸政趙宋」的鋪墊。
從客觀的角度看,他最大的「罪過」,就是沒有選擇「殉國」。如果他當初像其他忠烈之士一樣自殺,他就能得到「忠臣」的美名,但他可能就無法保住汴梁城的安寧,無法讓玉璽傳到趙構手中。
他的悲劇,在於他選擇了「活下去,做點事」的艱難道路,這在當時的「道德潔癖」環境下,是絕對不被允許的。
張邦昌,是靖康之變中,被歷史和道德判了「死刑」的複雜人物。 他那33天的「皇帝」經歷,成為了一個永遠的「政治污點」,抹殺了他所有的努力和掙扎。
他的故事,讓人深思:在民族存亡的時刻,一個文人的「屈辱求生」,到底是不是一種變相的「救國」? 歷史和後世,最終只記住了他的「黃袍加身」,而遺忘了他的「心不甘情不願」。
趙構見到張邦昌,心情是非常複雜的。
一方面,他知道張邦昌的「傀儡皇帝」生涯,確實是金人逼迫的結果;另一方面,張邦昌主動歸政、奉上玉璽,為南宋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沒有張邦昌在汴梁的「代理」,京城可能早就被徹底洗劫一空,趙構的繼位也不會如此順利。
趙構不是一個傻瓜,他懂得其中的利害關係。 如果他立刻殺了張邦昌,不僅顯得自己「不仁不義」,更重要的是,會向那些曾經在金人威逼下「委曲求全」的舊臣發出一個危險的信號:投降或屈從金人者,一律殺無赦。
這只會讓更多的人,徹底倒向金人。
因此,趙構做出了一個「政治上最正確」的決定:赦免張邦昌。他封張邦昌為同安郡王,表面上給予了極高的禮遇。
張邦昌暫時逃過了一劫,他的心頭大石似乎落了下來。他以為自己的「曲線救國」策略成功了,用33天的屈辱,換來了自己的生路,也換來了南宋的喘息。
然而,他低估了「文人士大夫」的道德標準,也低估了「主戰派」的政治力量。
李綱的怒火,一個繞不過的道德困境
張邦昌雖然得到了皇帝趙構的赦免,但朝堂上的「主戰派」,卻絕不答應。其中,最堅決、最憤怒的人,就是當時力主抗金的宰相李綱。
在李綱等一眾「鐵骨錚錚」的士大夫眼中,「叛國」就是死罪,無論你有什麼苦衷,無論你做了什麼貢獻,你登基的那一刻,就是對趙宋皇室最大的背叛和羞辱!
「名節」重於泰山,生死輕於鴻毛。 這是宋朝文人的普遍價值觀。在他們看來,張邦昌應該像那些忠烈之士一樣,寧死不屈,以身殉國,而不是為了苟活,去當金人的「傀儡」。
李綱堅決上奏,要求嚴懲張邦昌。
他的理由非常簡單而有力:張邦昌的「僭越稱帝」,是國家之恥,如果不對其嚴懲,如何能震懾天下叛臣?如何能挽救趙宋王朝的衰落形象?
李綱的堅持,代表了主流的道德和政治正確。趙構雖然想保張邦昌,但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和士大夫群體的憤怒,他開始動搖。
更要命的是,有人告發張邦昌在當「皇帝」期間,玷污了皇宮裡的宮人。這個指控,讓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張邦昌,徹底失去了道德上的支持。一個為保全性命而屈從於敵人的大臣,竟然還做出玷污宮人的醜事,這在道德上是絕對無法被接受的。
在李綱的堅持和輿論的壓力下,趙構最終無法抗衡。他被迫對張邦昌進行「處理」。建炎元年六月(1127年7月),張邦昌被貶往潭州(今湖南長沙)「安置」,美其名曰是「避禍」,實際上是流放。
張邦昌的命運,被政治和道德的雙重絞索,越勒越緊。 他那33天的「皇帝」經歷,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一個永遠無法洗清的污點。他雖然人在潭州,但心知肚明,自己的生命,已經進入了倒計時。
賜死潭州,一生的掙扎化為一聲嘆息
被貶到潭州之後,張邦昌的日子,過得異常屈辱和艱難。他的行動受到嚴格監視,一舉一動都要向朝廷報告。
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,很快就來了。
金人得知張邦昌被貶的消息後,非常不滿。他們威脅南宋朝廷,稱「如果張邦昌被廢,我們就要再次南侵!」
金人的這番話,無疑是將張邦昌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。對於趙構來說,張邦昌的「政治價值」已經徹底消失,反而成了「招惹金人的麻煩」。
一個活著的張邦昌,是金人南侵的藉口;一個死去的張邦昌,才能平息朝堂的怒火和金人的藉口。
建炎元年九月,宋高宗趙構下詔,將張邦昌賜死。
接到詔書的張邦昌,讀罷之後,「徘徊退避,不忍自盡」。他是一個文人,雖然經歷了人生的巨大起落,但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,他仍然心有不甘。
他一生都在掙扎,在忠君與保城之間掙扎,在道德與苟活之間掙扎。最終,他所有的掙扎,都化為了一聲嘆息。
在執行官的逼迫下,張邦昌最終登上了潭州城內天寧寺的平楚樓,自縊身亡。
這個做了33天皇帝的男人,用自己的死,為南宋的建立獻出了最後的「祭品」。 他的死,既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,也是宋朝文人「名節」至上價值觀的犧牲品。
他死後,趙構為了安撫他身後的親人,也為了顯示自己的「仁慈」,曾下詔禮尊張邦昌,讓他的子孫親屬獲得錄用。但這並不能改變張邦昌在歷史上的悲劇性地位。
死後千年罵名,老家祖墳都不要他
張邦昌死了,但他的罵名,才剛剛開始。
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歲月里,「張邦昌」這個名字,成了「漢奸」、「賣國賊」的代名詞。他是南宋人心中最痛的恥辱,是「靖康之恥」中最鮮活的「叛國者」形象。
宋朝的史官們,秉承著「名節」至上的原則,將張邦昌的所作所為,毫不留情地釘在了史書上。他的一切苦衷和努力,都被那33天的「皇帝」經歷所掩蓋。
後世的文學作品、戲曲小說,更是對張邦昌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醜化。 在民間故事裡,他被塑造成一個貪生怕死、趨炎附勢的小人。
這一罵,就是整整九百年。 直到今天,只要提到靖康之變和偽楚政權,張邦昌的名字,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「反面教材」。
更讓人唏噓的是,張邦昌死後,連回老家安葬都成了一種奢望。
張邦昌是河北東路永靜軍東光縣(今河北滄州)人。當他的家人打算將他的遺骸運回老家,安葬進張氏祖墳時,遭到了老家鄉親們和族人的強烈拒絕!
「一個曾僭越稱帝、辜負大宋的叛臣,沒資格入葬我們張氏祖墳!」 鄉親們義憤填膺,認為讓張邦昌入土為安,是對祖宗的「大不敬」。
這是何等的悲哀和屈辱! 張邦昌一輩子都在為自己的名節掙扎,到頭來,不僅自己被賜死,連死後都落得「無家可歸,祖墳不容」的下場。
他用33天的皇帝生涯,換來了一個家族長達數百年的恥辱。 他本想「曲線救國」,卻最終成了「兩邊不討好」的千古罪人。
張邦昌的「不得不」
回過頭來看張邦昌的一生,我們不能簡單地用「忠臣」或「奸賊」來給他定性。他的故事,是一個時代悲劇下的個人悲劇。
張邦昌的「不得不」,反映了宋朝文官在民族大義和個人存亡之間的巨大困境。他沒有武將的英勇和決絕,也沒有士大夫的堅貞和赴死,他只是一個渴望和平、想要保全城池的文人宰相。
在金人兵臨城下,宋徽宗、宋欽宗束手無策的情況下,誰來保住這座城?誰來為城中的百姓爭取一線生機?
張邦昌用自己的名節和性命,為汴梁城換取了暫時的安寧。 他在位期間,沒有主動殘害宋朝宗室,沒有大肆屠殺百姓,反而做了「歸政趙宋」的鋪墊。
從客觀的角度看,他最大的「罪過」,就是沒有選擇「殉國」。如果他當初像其他忠烈之士一樣自殺,他就能得到「忠臣」的美名,但他可能就無法保住汴梁城的安寧,無法讓玉璽傳到趙構手中。
他的悲劇,在於他選擇了「活下去,做點事」的艱難道路,這在當時的「道德潔癖」環境下,是絕對不被允許的。
張邦昌,是靖康之變中,被歷史和道德判了「死刑」的複雜人物。 他那33天的「皇帝」經歷,成為了一個永遠的「政治污點」,抹殺了他所有的努力和掙扎。
他的故事,讓人深思:在民族存亡的時刻,一個文人的「屈辱求生」,到底是不是一種變相的「救國」? 歷史和後世,最終只記住了他的「黃袍加身」,而遺忘了他的「心不甘情不願」。
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