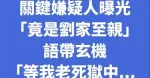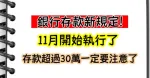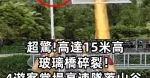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李自成當了42天皇帝,42天裡他都乾了什麼?四件事把他送上絕路

3/3
他自認推翻了明王朝,又有數十萬鐵騎環繞,自然應當「論功行賞」,給兄弟們一個交代。
可他忘了,江山未穩,根基未立,此時的獎賞不是恩賜,而是賭注,一旦賭錯方向,便是滿盤皆輸。
大順軍是從飢餓線上的百姓拼殺而來,一路走來,吃的是草根樹皮,住的是山林茅屋。
打仗時人人拚命,搶糧時個個如狼。
李自成自己就開了一個壞頭。
他在皇宮大開「封賞大會」,將明朝皇族留下的珍寶一箱箱抬出,金杯銀盞、珠鏈玉佩,一律「按功分賜」。
在分贓之際,李自成下了一道「賞金令」,將領每人百兩銀,兵卒每人十兩,未來若再有戰功,「再議賞銀三成」。
這一「賞」,賞得全軍血脈賁張,卻也讓他們心中種下了貪慾的種子。
士兵們嘗到甜頭後,軍紀頓時鬆懈。
曾經風餐露宿、追擊千里的闖軍士兵,如今在富麗堂皇的北京街巷中,變得懶散、浮躁。
李自成雖然設有「將令」,但賞銀一出,人人都想邀功搶頭功,部隊爭功諉過、擅動軍隊、擅入民宅的事屢見不鮮,軍法根本無法約束。
不少士兵公開叫囂:「皇帝給你做,金銀給我們分。」
這話一傳出,原本就士氣浮動的軍營中更是炸了鍋。
有的兵卒乾脆不練兵、不巡邏,窩在分來的宅子中日日飲酒作樂,還有的將領帶頭索賞,若李自成稍有推遲,便扯起臉來:
「若非我家兄弟死戰,哪有你這江山?」
如此風氣之下,兵心散了。
原本打仗不要命的義軍,如今人人懷揣金銀、腰纏珠寶,哪還肯上前線?
有一回,李自成命數營出征山海關一帶防守,有士兵當場頂撞:
「若戰死,此寶豈非落人之手?」
原本一聲號令就能調動萬軍,如今卻要李自成一一承諾「凱旋再賞」、「家屬撫恤」等,才勉強湊出一支「勉強動身」的隊伍。
原本的「同袍之義」,徹底被銀兩貪慾撕裂殆盡。
整個軍隊已無紀律可言,仿佛一群身著盔甲的土匪,守的不是城,而是自己搶來的財物。
李自成看在眼裡,卻無力回天這群曾願為他拚命的兄弟,如今只剩下銅臭味權色心。
那一把金銀,是戰利品,也是亡國劍。
官紳痛恨因酷政
打天下靠的是刀槍,坐天下靠的卻是人心,李自成不光亂了自己和軍隊,也惹了那批曾主導政權運作、掌握資源與話語權的文官士紳。
最初,許多明朝舊臣對李自成沒有太大敵意。
朝中多位大員甚至主動上表,請求為大順效力。
他們中有人希望藉助新政權一展所學,也有人只是為求自保,順應時勢而已。
但無論初衷如何,這些原本掌控京城命脈的士紳階層,本可為李自成的新政權提供穩定的行政力量和政治認同。
可惜,李自成並不懂這門「坐天下」的學問。
在他的觀念中,文官便是前朝的爪牙,富紳便是剝削百姓的罪魁禍首。
他對官紳的認知,仍停留在草寇年代「搶大戶、燒田契」的階段。
他頒布的一紙「助餉令」,將所有文武百官按品級分為十數檔,內閣大學士需交十萬兩銀,六部尚書交七萬,九卿五萬,翰林一萬,普通吏員也不得少於千兩。
至於勛貴王侯,則「無定數」,簡單來說,能交多少是你本事,交不出,命便休矣。
文官們自古多清貧,雖有俸祿,但家無餘財者不在少數。
更有甚者,清流派大臣向來以清廉自居,一聽「捐銀助餉」四字,便如割肉剜心。
可李自成哪裡聽得進去這些?他任命劉宗敏為「追贓督辦」,大開酷刑,命人制了五千副夾棍,設下「拷銀府」,將一眾舊臣像牲畜一樣拖進刑堂。
那些原本心懷僥倖、想在新政權中繼續效力的士紳們,這下也徹底死心了。
李自成不僅不給他們以禮相待,反倒視之為待宰羔羊,一切以「追贓」為先。
一些士人憤然自盡,另一些則佯作順從,暗中聯絡清軍、明軍殘部,尋求反撲機會。
就連普通的民間書生,也對這位「闖王皇帝」失去了最後的尊重。
大順朝廷朝會上,原本應有鐘鳴鼓樂、文臣列隊,如今卻空曠冷清,只見李自成一人獨坐龍椅,面前不過牛金星等幾個謀士。
朝中無人敢進諫,無人敢正言,人人只求自保,避禍為上。
與此同時,李自成對百姓也下達了「均貧富」的命令,要求城中富戶交出財產、田契、糧食。
他本想以此收買人心,可執行者卻將這紙政令玩成了徹底的「掠奪令」。
凡是有些家底的家庭,無論清白與否,財產都被洗劫一空。
那些一夜之間被推倒的富戶,不再信大順政權,紛紛聯絡舊明官員或暗通清軍,謀求「重立天命」。
李自成此舉,不僅得罪了文官集團,也將傳統士紳群體一併推向對立面。
要知道,這些人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力量,掌握著地方資源、鄉里威望、知識系統和輿論話語權。
他一朝得罪,等於割斷了大順政權的「治理經脈」。
就這樣,大順政權在京城的根基,尚未打穩便已坍塌。
致命失誤誤時局
一點又一滴的錯誤積累,但要說李自成最大的致命失誤之一,便是對清軍的判斷天真至極。
彼時的關外女真,已改號「清」,清廷雖然尚未穩固,卻早已虎視眈眈地盯著中原這一塊肥肉。
但李自成對此毫無警惕,他以為清軍與自己同為「反明陣營」,雙方尚可坐而論道,共謀大業。
事實上,清軍李自成之間,沒有絲毫信任,也從未將這個「農民皇帝」視作盟友。
清廷之計,自始至終,只有一條,漁翁得利,南下奪國。
而李自成,卻將所有防禦部署的重心放在了南方殘明勢力身上,對北方山海關一線,僅派唐通駐守。
他甚至親信地對牛金星說:「女真跋涉千里,豈能當下即戰?山海關有我人,足矣。」
這一句話,幾乎把自己後路徹底掘斷。
更荒唐的是,李自成不僅沒有主動派人籠絡關外勢力,反倒因為一樁「尋常事」,徹底斷送了一個關鍵人物,那就是吳三桂。
吳三桂當時正駐守山海關,手握重兵,本是大明最後的邊關長城。
面對李自成攻占北京、崇禎自縊的變局,他曾猶豫不決。
甚至,他一度準備歸順大順政權,只求保家安民,而李自成最初也願意給他一封「封侯令」,許他高爵厚祿。
可變數,往往就在細節中。
吳三桂派人入京商議歸順事宜,沒想到卻得知,李自成不僅軟禁了他的父親吳襄,還強行掠走了他最寵愛的陳圓圓。
據說,吳襄被人拷打索銀,幾近吐血,而陳圓圓,則成了劉宗敏府上的「夜宴之賓」。
他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」,其實怒的豈止是紅顏,更是尊嚴。
就在李自成還在宮中調兵遣將、籌辦登基典禮時,吳三桂已連夜重新占領山海關,並向清軍使者遞出了求援信。
這封信,便是通向北京城的大門鑰匙。
多爾袞原本還在擔心山海關難破,如今大門主動打開,還有一個大明降將帶路,天賜之機,不可不取。
一場真正意義上的「亡國之戰」已悄然展開。
而此時的李自成,依舊陷在「皇帝夢」里不能自拔。
他直到吳三桂反水的消息傳來,才如夢初醒,李自成急急趕往前線,結果遭遇清軍鐵騎壓境,一戰未及交鋒,陣腳先亂。
兵敗如山倒,大順軍死傷慘重,李自成只能倉皇逃回北京。
可就當全城還指望「皇帝能守」,李自成卻下了一道令人寒心的命令,放棄北京。
北京百姓憤怒了,原本尚有一絲幻想的新朝主心骨,如今卻成了丟盔棄甲的逃兵。
與此同時,李自成在西南的戰略失誤,也暴露無遺。
張獻忠率領的大西軍,本是與李自成起義同期的勁旅,若兩軍合兵,尚可南北策應、共抗清軍。
可李自成自恃為「正統」,不僅不肯主動議和,還派兵南下,插手四川地方官員的任命,與張獻忠勢力產生衝突。
最終,兩位本可並肩抗敵的義軍領袖,反目成仇,互不支援。
從戰略誤判到人事錯用,從內部腐化到外部輕敵,李自成親手把一手好牌,打成了徹底的爛局。
當李自成率殘軍撤出北京,紫禁城的大門再次為外族打開。
自入京到敗逃,僅僅42天。
李自成的帝王夢,毀於他自己一步步錯下的棋。
可他忘了,江山未穩,根基未立,此時的獎賞不是恩賜,而是賭注,一旦賭錯方向,便是滿盤皆輸。
大順軍是從飢餓線上的百姓拼殺而來,一路走來,吃的是草根樹皮,住的是山林茅屋。
打仗時人人拚命,搶糧時個個如狼。
李自成自己就開了一個壞頭。
他在皇宮大開「封賞大會」,將明朝皇族留下的珍寶一箱箱抬出,金杯銀盞、珠鏈玉佩,一律「按功分賜」。
在分贓之際,李自成下了一道「賞金令」,將領每人百兩銀,兵卒每人十兩,未來若再有戰功,「再議賞銀三成」。
這一「賞」,賞得全軍血脈賁張,卻也讓他們心中種下了貪慾的種子。
士兵們嘗到甜頭後,軍紀頓時鬆懈。
曾經風餐露宿、追擊千里的闖軍士兵,如今在富麗堂皇的北京街巷中,變得懶散、浮躁。
李自成雖然設有「將令」,但賞銀一出,人人都想邀功搶頭功,部隊爭功諉過、擅動軍隊、擅入民宅的事屢見不鮮,軍法根本無法約束。
不少士兵公開叫囂:「皇帝給你做,金銀給我們分。」
這話一傳出,原本就士氣浮動的軍營中更是炸了鍋。
有的兵卒乾脆不練兵、不巡邏,窩在分來的宅子中日日飲酒作樂,還有的將領帶頭索賞,若李自成稍有推遲,便扯起臉來:
「若非我家兄弟死戰,哪有你這江山?」
如此風氣之下,兵心散了。
原本打仗不要命的義軍,如今人人懷揣金銀、腰纏珠寶,哪還肯上前線?
有一回,李自成命數營出征山海關一帶防守,有士兵當場頂撞:
「若戰死,此寶豈非落人之手?」
原本一聲號令就能調動萬軍,如今卻要李自成一一承諾「凱旋再賞」、「家屬撫恤」等,才勉強湊出一支「勉強動身」的隊伍。
原本的「同袍之義」,徹底被銀兩貪慾撕裂殆盡。
整個軍隊已無紀律可言,仿佛一群身著盔甲的土匪,守的不是城,而是自己搶來的財物。
李自成看在眼裡,卻無力回天這群曾願為他拚命的兄弟,如今只剩下銅臭味權色心。
那一把金銀,是戰利品,也是亡國劍。
官紳痛恨因酷政
打天下靠的是刀槍,坐天下靠的卻是人心,李自成不光亂了自己和軍隊,也惹了那批曾主導政權運作、掌握資源與話語權的文官士紳。
最初,許多明朝舊臣對李自成沒有太大敵意。
朝中多位大員甚至主動上表,請求為大順效力。
他們中有人希望藉助新政權一展所學,也有人只是為求自保,順應時勢而已。
但無論初衷如何,這些原本掌控京城命脈的士紳階層,本可為李自成的新政權提供穩定的行政力量和政治認同。
可惜,李自成並不懂這門「坐天下」的學問。
在他的觀念中,文官便是前朝的爪牙,富紳便是剝削百姓的罪魁禍首。
他對官紳的認知,仍停留在草寇年代「搶大戶、燒田契」的階段。
他頒布的一紙「助餉令」,將所有文武百官按品級分為十數檔,內閣大學士需交十萬兩銀,六部尚書交七萬,九卿五萬,翰林一萬,普通吏員也不得少於千兩。
至於勛貴王侯,則「無定數」,簡單來說,能交多少是你本事,交不出,命便休矣。
文官們自古多清貧,雖有俸祿,但家無餘財者不在少數。
更有甚者,清流派大臣向來以清廉自居,一聽「捐銀助餉」四字,便如割肉剜心。
可李自成哪裡聽得進去這些?他任命劉宗敏為「追贓督辦」,大開酷刑,命人制了五千副夾棍,設下「拷銀府」,將一眾舊臣像牲畜一樣拖進刑堂。
那些原本心懷僥倖、想在新政權中繼續效力的士紳們,這下也徹底死心了。
李自成不僅不給他們以禮相待,反倒視之為待宰羔羊,一切以「追贓」為先。
一些士人憤然自盡,另一些則佯作順從,暗中聯絡清軍、明軍殘部,尋求反撲機會。
就連普通的民間書生,也對這位「闖王皇帝」失去了最後的尊重。
大順朝廷朝會上,原本應有鐘鳴鼓樂、文臣列隊,如今卻空曠冷清,只見李自成一人獨坐龍椅,面前不過牛金星等幾個謀士。
朝中無人敢進諫,無人敢正言,人人只求自保,避禍為上。
與此同時,李自成對百姓也下達了「均貧富」的命令,要求城中富戶交出財產、田契、糧食。
他本想以此收買人心,可執行者卻將這紙政令玩成了徹底的「掠奪令」。
凡是有些家底的家庭,無論清白與否,財產都被洗劫一空。
那些一夜之間被推倒的富戶,不再信大順政權,紛紛聯絡舊明官員或暗通清軍,謀求「重立天命」。
李自成此舉,不僅得罪了文官集團,也將傳統士紳群體一併推向對立面。
要知道,這些人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力量,掌握著地方資源、鄉里威望、知識系統和輿論話語權。
他一朝得罪,等於割斷了大順政權的「治理經脈」。
就這樣,大順政權在京城的根基,尚未打穩便已坍塌。
致命失誤誤時局
一點又一滴的錯誤積累,但要說李自成最大的致命失誤之一,便是對清軍的判斷天真至極。
彼時的關外女真,已改號「清」,清廷雖然尚未穩固,卻早已虎視眈眈地盯著中原這一塊肥肉。
但李自成對此毫無警惕,他以為清軍與自己同為「反明陣營」,雙方尚可坐而論道,共謀大業。
事實上,清軍李自成之間,沒有絲毫信任,也從未將這個「農民皇帝」視作盟友。
清廷之計,自始至終,只有一條,漁翁得利,南下奪國。
而李自成,卻將所有防禦部署的重心放在了南方殘明勢力身上,對北方山海關一線,僅派唐通駐守。
他甚至親信地對牛金星說:「女真跋涉千里,豈能當下即戰?山海關有我人,足矣。」
這一句話,幾乎把自己後路徹底掘斷。
更荒唐的是,李自成不僅沒有主動派人籠絡關外勢力,反倒因為一樁「尋常事」,徹底斷送了一個關鍵人物,那就是吳三桂。
吳三桂當時正駐守山海關,手握重兵,本是大明最後的邊關長城。
面對李自成攻占北京、崇禎自縊的變局,他曾猶豫不決。
甚至,他一度準備歸順大順政權,只求保家安民,而李自成最初也願意給他一封「封侯令」,許他高爵厚祿。
可變數,往往就在細節中。
吳三桂派人入京商議歸順事宜,沒想到卻得知,李自成不僅軟禁了他的父親吳襄,還強行掠走了他最寵愛的陳圓圓。
據說,吳襄被人拷打索銀,幾近吐血,而陳圓圓,則成了劉宗敏府上的「夜宴之賓」。
他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」,其實怒的豈止是紅顏,更是尊嚴。
就在李自成還在宮中調兵遣將、籌辦登基典禮時,吳三桂已連夜重新占領山海關,並向清軍使者遞出了求援信。
這封信,便是通向北京城的大門鑰匙。
多爾袞原本還在擔心山海關難破,如今大門主動打開,還有一個大明降將帶路,天賜之機,不可不取。
一場真正意義上的「亡國之戰」已悄然展開。
而此時的李自成,依舊陷在「皇帝夢」里不能自拔。
他直到吳三桂反水的消息傳來,才如夢初醒,李自成急急趕往前線,結果遭遇清軍鐵騎壓境,一戰未及交鋒,陣腳先亂。
兵敗如山倒,大順軍死傷慘重,李自成只能倉皇逃回北京。
可就當全城還指望「皇帝能守」,李自成卻下了一道令人寒心的命令,放棄北京。
北京百姓憤怒了,原本尚有一絲幻想的新朝主心骨,如今卻成了丟盔棄甲的逃兵。
與此同時,李自成在西南的戰略失誤,也暴露無遺。
張獻忠率領的大西軍,本是與李自成起義同期的勁旅,若兩軍合兵,尚可南北策應、共抗清軍。
可李自成自恃為「正統」,不僅不肯主動議和,還派兵南下,插手四川地方官員的任命,與張獻忠勢力產生衝突。
最終,兩位本可並肩抗敵的義軍領袖,反目成仇,互不支援。
從戰略誤判到人事錯用,從內部腐化到外部輕敵,李自成親手把一手好牌,打成了徹底的爛局。
當李自成率殘軍撤出北京,紫禁城的大門再次為外族打開。
自入京到敗逃,僅僅42天。
李自成的帝王夢,毀於他自己一步步錯下的棋。
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