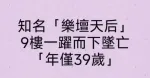10/10
下一頁
花費上億台幣!!! 台灣大咖「包養100多位情婦」風光無限 生命最後「卻落得人財兩空」在孤獨中斷氣...

10/10
他臨終時身邊真正還在的人很少:兒子、姐姐,還有一個叫小潘潘的乾女兒,醫院走廊也不像豪門落幕那種場面,沒有花籃排隊、沒有人哭成一片,更多的是冷清。
相反,盯著他的還有債權人,那種眼神像在算帳,恨不得從他身上再摳出點剩餘價值。
所以他表面是死於病,實際更像死在自己那套「全靠算計和金錢維繫」的人生模式里:風光的時候一呼百應,倒下的時候無人問津。
他花了一輩子、砸了二十億,把熱鬧買到極致,也把孤獨買到極致,他這一生像個誇張的反面教材:錢能讓人圍著你轉,能把場面撐得很大,但錢買不到真正願意陪你到最後的人。
到了心電圖拉直線那一刻,曾經的豪奢和荒唐都沒了意義,剩下的只是一地雞毛,留給世人的只有那張永遠還不起的欠稅單,和一聲沉重的嘆息。
他用一生詮釋資本的輝煌,也用最後的日子詮釋金錢的冰冷⋯⋯。
相反,盯著他的還有債權人,那種眼神像在算帳,恨不得從他身上再摳出點剩餘價值。
所以他表面是死於病,實際更像死在自己那套「全靠算計和金錢維繫」的人生模式里:風光的時候一呼百應,倒下的時候無人問津。
他花了一輩子、砸了二十億,把熱鬧買到極致,也把孤獨買到極致,他這一生像個誇張的反面教材:錢能讓人圍著你轉,能把場面撐得很大,但錢買不到真正願意陪你到最後的人。
到了心電圖拉直線那一刻,曾經的豪奢和荒唐都沒了意義,剩下的只是一地雞毛,留給世人的只有那張永遠還不起的欠稅單,和一聲沉重的嘆息。
他用一生詮釋資本的輝煌,也用最後的日子詮釋金錢的冰冷⋯⋯。
 呂純弘 • 16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66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4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5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老臘肉 • 5K次觀看
老臘肉 • 5K次觀看 老臘肉 • 5K次觀看
老臘肉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老臘肉 • 95K次觀看
老臘肉 • 95K次觀看 老臘肉 • 2K次觀看
老臘肉 • 2K次觀看 老臘肉 • 4K次觀看
老臘肉 • 4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