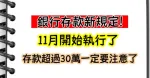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李煜的最後絕唱:毒酒送來前寫下這 56 字,如今人人掛在嘴邊

2/3
子時將近,酒被送來。史料稱之為「牽機藥」,服下之後,筋骨抽搐,頭足相就,死狀慘烈。李煜接過酒杯時,或許並未猶豫。三年的幽禁生活,早已將他推到極限。對他而言,死亡反倒是一種終結。
就在這之前,他寫下了最後一首詞。沒有刻意鋪陳,也沒有激烈控訴,只是平靜地回望一生。
「春花秋月何時了,往事知多少。」
時間在他筆下,不再是流逝的刻度,而是不斷回返的痛感。季節依舊輪迴,而往事卻再也回不來。
「小樓昨夜又東風,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」
東風照舊,月色如常,真正改變的,是站在月下的人。金陵仍在,卻已與他無關。
「雕欄玉砌應猶在,只是朱顏改。」
他沒有說宮殿毀壞,只說人變了。物或許還能保留原樣,人卻早已散盡、老去、死去。
「問君能有幾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
這一句,將無法計量的情緒,化作奔流不息的江水。愁不止、不絕,也無法回頭。
就在這之前,他寫下了最後一首詞。沒有刻意鋪陳,也沒有激烈控訴,只是平靜地回望一生。
「春花秋月何時了,往事知多少。」
時間在他筆下,不再是流逝的刻度,而是不斷回返的痛感。季節依舊輪迴,而往事卻再也回不來。
「小樓昨夜又東風,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」
東風照舊,月色如常,真正改變的,是站在月下的人。金陵仍在,卻已與他無關。
「雕欄玉砌應猶在,只是朱顏改。」
他沒有說宮殿毀壞,只說人變了。物或許還能保留原樣,人卻早已散盡、老去、死去。
「問君能有幾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
這一句,將無法計量的情緒,化作奔流不息的江水。愁不止、不絕,也無法回頭。
 呂純弘 • 7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9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7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