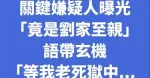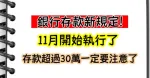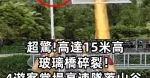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1960年閻錫山去世,臨終前留下奇怪遺言:我死後不許你們放聲大哭

3/3
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,他依然在算計。
他禁止家人放聲大哭,就是要主動剝離自己身後事的一切「情緒」色彩,把它變成一場平淡、安靜、無人可以做文章的告別儀式。
他用這種方式告訴蔣介石:我閻錫山已經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,我的家人和部下對我沒有任何政治幻想,他們甚至連一場像樣的悲傷都不敢有。
從「山西王」到孤島隱士,一輩子都在走鋼絲
閻錫山的這句遺言,是他一生處世哲學的終極體現。
回看閻錫山的一生,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永遠在走鋼絲的人,他的核心信條只有一個:存在就是真理。
為了存在下去,他可以變換任何姿態。
閻錫山出生於山西的商人家庭,骨子裡就帶著商人的精明與投機。
1905年,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,這是一筆政治投資。
辛亥革命爆發,他立刻發動太原起義,年僅28歲就當上山西都督,這筆投資獲得了驚人回報。
此後,他開啟了在各路軍閥夾縫中求生的「牆頭草」生涯。
面對強大的袁世凱,他表面效忠,送上兩萬大洋,暗中卻和孫中山保持聯繫。
袁世凱去世後,他又迅速倒向段祺瑞。
北伐戰爭初期,他持觀望態度,直到看清局勢才選擇「擁蔣」。
他就像一個高超的平衡木選手,在中央與地方、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來回搖擺,總能找到那個最有利於自己生存的支點。
這種手腕,讓山西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裡,保持了長達數十年的相對穩定。
他對山西的建設也充滿了這種「商人」式的算計。
他修鐵路、開煤礦、辦教育、建兵工廠,把山西打造成了「模範省」。
但這些建設的首要目的,都是為了服務於他的軍事和政治統治。
修路是為了方便運輸軍火,辦教育是為了培養忠於自己的幹部。
他的鄉土情結與他的權力慾望,始終緊密地捆綁在一起。
然而,鋼絲總有走到頭的時候。
1930年的中原大戰,是閻錫山一生最大的政治豪賭。
他先是聯合蔣介石,將馮玉祥騙到山西軟禁;隨後又意識到自己也是蔣介石的目標,轉而聯合馮玉祥、李宗仁反蔣,一度問鼎中原。
可張學良的東北軍入關支持蔣介石,讓閻錫山的算盤徹底落空。
他兵敗下野,被迫前往大連避難。
這次失敗讓他深刻認識到,個人的權謀終究抵不過歷史的大勢。
從那一刻起,閻錫山變得更加謹小慎微。
抗日戰爭中,他一面組織抗日,一面又極力保存實力。
到了台灣,這種謹慎更是發展到了極致。
他深居簡出,讀書寫作,將自己徹底變成一個與世無爭的「哲學家」。
他一生都在為自己和自己的勢力尋找安全的「掩體」。
臨終前,他為家人準備的最後一個、也是最堅固的掩體,就是那句「不要放聲大哭」的遺言。
這不僅是對世態炎涼的洞察,更是他一生謹慎哲學的最終貫徹。
他知道自己死後,真心哭泣的人不多,逢場作戲的人不少。
他索性主動要求「靜音」,免去這場虛偽的儀式,也斷絕了任何人藉此生事的可能。
閻錫山的一生,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現代史。
他以一個地方軍閥的身份,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屹立數十年,其政治手腕和生存智慧確實非凡。
他用近四十年的時間,將貧窮的山西打造成了模範省份;又用了最後十年的時間,將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島。
從權力的巔峰到孤寂的晚景,他用自己的一生,註解了「存在就是真理」這句信條。
他禁止家人放聲大哭,就是要主動剝離自己身後事的一切「情緒」色彩,把它變成一場平淡、安靜、無人可以做文章的告別儀式。
他用這種方式告訴蔣介石:我閻錫山已經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,我的家人和部下對我沒有任何政治幻想,他們甚至連一場像樣的悲傷都不敢有。
從「山西王」到孤島隱士,一輩子都在走鋼絲
閻錫山的這句遺言,是他一生處世哲學的終極體現。
回看閻錫山的一生,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永遠在走鋼絲的人,他的核心信條只有一個:存在就是真理。
為了存在下去,他可以變換任何姿態。
閻錫山出生於山西的商人家庭,骨子裡就帶著商人的精明與投機。
1905年,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,這是一筆政治投資。
辛亥革命爆發,他立刻發動太原起義,年僅28歲就當上山西都督,這筆投資獲得了驚人回報。
此後,他開啟了在各路軍閥夾縫中求生的「牆頭草」生涯。
面對強大的袁世凱,他表面效忠,送上兩萬大洋,暗中卻和孫中山保持聯繫。
袁世凱去世後,他又迅速倒向段祺瑞。
北伐戰爭初期,他持觀望態度,直到看清局勢才選擇「擁蔣」。
他就像一個高超的平衡木選手,在中央與地方、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來回搖擺,總能找到那個最有利於自己生存的支點。
這種手腕,讓山西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裡,保持了長達數十年的相對穩定。
他對山西的建設也充滿了這種「商人」式的算計。
他修鐵路、開煤礦、辦教育、建兵工廠,把山西打造成了「模範省」。
但這些建設的首要目的,都是為了服務於他的軍事和政治統治。
修路是為了方便運輸軍火,辦教育是為了培養忠於自己的幹部。
他的鄉土情結與他的權力慾望,始終緊密地捆綁在一起。
然而,鋼絲總有走到頭的時候。
1930年的中原大戰,是閻錫山一生最大的政治豪賭。
他先是聯合蔣介石,將馮玉祥騙到山西軟禁;隨後又意識到自己也是蔣介石的目標,轉而聯合馮玉祥、李宗仁反蔣,一度問鼎中原。
可張學良的東北軍入關支持蔣介石,讓閻錫山的算盤徹底落空。
他兵敗下野,被迫前往大連避難。
這次失敗讓他深刻認識到,個人的權謀終究抵不過歷史的大勢。
從那一刻起,閻錫山變得更加謹小慎微。
抗日戰爭中,他一面組織抗日,一面又極力保存實力。
到了台灣,這種謹慎更是發展到了極致。
他深居簡出,讀書寫作,將自己徹底變成一個與世無爭的「哲學家」。
他一生都在為自己和自己的勢力尋找安全的「掩體」。
臨終前,他為家人準備的最後一個、也是最堅固的掩體,就是那句「不要放聲大哭」的遺言。
這不僅是對世態炎涼的洞察,更是他一生謹慎哲學的最終貫徹。
他知道自己死後,真心哭泣的人不多,逢場作戲的人不少。
他索性主動要求「靜音」,免去這場虛偽的儀式,也斷絕了任何人藉此生事的可能。
閻錫山的一生,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現代史。
他以一個地方軍閥的身份,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屹立數十年,其政治手腕和生存智慧確實非凡。
他用近四十年的時間,將貧窮的山西打造成了模範省份;又用了最後十年的時間,將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島。
從權力的巔峰到孤寂的晚景,他用自己的一生,註解了「存在就是真理」這句信條。
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6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6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5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4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4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7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4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