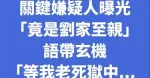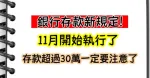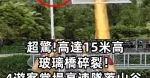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真正「文武雙全」,文人里最能打,武將里最有文化,他結局太可惜

3/3
想想這畫面吧:一個本應是「文縐縐」的掌書記,帶著幾個弟兄,單槍匹馬深入敵後,追砍叛徒,殺人奪印,再衝出來……
這膽氣、這武力值、這執行力,簡直是天神下凡!這一戰,讓辛棄疾在義軍中聲威大振,也初步顯露了他絕非僅靠筆墨吃飯的驚人一面。但這,竟然還不是他最巔峰的表演!
更大的風暴,很快就要降臨在他身上。
南歸的猛虎
帶著活捉張安國的傳奇戰績,年僅23歲的辛棄疾終於踏上了南宋的土地。這個在金人鐵蹄下長大的「歸正人」,滿腔熱血只想為故國效力,收復中原。他以為到了「自己人」的朝廷,就能大展拳腳。現實卻給了他當頭一棒。
南宋朝廷對他這樣的「北來豪傑」,態度極其矛盾。一方面欣賞他的勇猛和能力,宋高宗趙構就親自接見了他,授予他江陰簽判的官職。另一方面,朝廷上下瀰漫著對金人根深蒂固的恐懼和主和苟安的氛圍。
像辛棄疾這樣敢打敢拼、堅決主戰的人物,反而成了「不穩定因素」,處處受猜忌、排擠。
辛棄疾哪管這些彎彎繞繞?他骨子裡就是個行動派。官職不大,照樣給朝廷上書!短短几年間,他寫出了震動朝野的《美芹十論》(又稱《御戎十論》)和《九議》。
這些可不是文人空談,而是實實在在的軍事戰略。他詳細分析金國「虛胖」的本質,地盤太大管不過來,民族壓迫太重人心不穩,這正是南宋反攻的絕佳機會。
他還具體規劃了南宋該如何積蓄力量、訓練精兵、籌措軍費,甚至提出了從山東出兵直搗河朔的北伐路線圖。
道理講得透徹,方案寫得紮實,結果呢?石沉大海。
主和派當道,皇帝也沒決心,這些凝聚了他心血和智慧的策論,最終被束之高閣。辛棄疾這才有點明白了,在南宋當官,光有本事和熱血遠遠不夠。
既然中央用不上力,他就在地方上使勁!機會來了。1179年,辛棄疾調任湖南安撫使,掌管一方軍政。
當時的湖南,地處南宋邊疆,西邊和南邊連著兩廣,再往外就是少數民族聚居的溪峒地區,山賊草寇經常作亂,治安極差,軍隊也疲軟不堪。
辛棄疾一看這情況,立刻拍板:必須練一支能打的精兵!他力排眾議,要在長沙馬殷營壘的故址上,打造一支新軍,這就是後來威震南方的「飛虎軍」。
建軍的難度超乎想像。樞密院(相當於中央軍委)里就有反對派,不斷給辛棄疾使絆子,想讓他幹不成,經費更是天文數字。
有人抓住這點,直接告到皇帝那裡,說他「聚斂民財」。皇帝一聽,趕緊發下金字牌,命令工程「立刻停止」!
換成別人,可能就認栽了。但他是辛棄疾!接到金牌,他面不改色地收起來,轉頭就對工程負責人下了死命令:「一個月!飛虎軍營柵必須建成!完不成,軍法處置!」
他親自調度,精打細算,甚至遇到連月陰雨、造瓦困難時,想出了讓居民每家獻出兩塊屋檐瓦的妙招,短短兩天就湊齊了二十萬片瓦。一個月後,軍營如期建成。
辛棄疾把工程報告和圖紙呈給皇帝,條理清晰,帳目明白,皇帝這才消了氣。這支飛虎軍,後來成了「雄鎮一方」、「江上諸軍之冠」的勁旅。
但辛棄疾的「硬核」作風,也徹底得罪了朝中權貴。1181年,飛虎軍建成不久,他就被扣上「用錢如泥沙,殺人如草芥」的罪名,罷官免職。
更憋屈的還在後頭。幾年後江西鬧大饑荒,朝廷又想起辛棄疾的辦事能力,派他去賑災。他一到災區,雷厲風行:貼出告示,宣布「囤糧不賣者流放,強買搶糧者斬首」!
接著拿出官府所有錢財,發動官民中有門路的人去外地買糧,承諾不收利息,月底運回平價銷售。很快,運糧船隊絡繹不絕,糧價應聲下跌,百姓得以活命。
這時鄰近的信州(今江西上饒)也鬧饑荒,太守謝源明求援。辛棄疾的部下都反對:我們自己還不夠呢!辛棄疾卻大手一揮:「都是大宋百姓,都是皇上的子民!」 當即調撥了三分之一糧船支援信州。
皇帝為此嘉獎了他,升了一級俸祿。可沒過多久,他又被言官彈劾,再次丟官。
一次次的起用,一次次的建功,又一次次的罷免……辛棄疾這隻北歸的猛虎,縱有裂石之爪、嘯谷之威,終究被死死困在了南宋朝廷這個精緻的牢籠里。
把刀劍熔進筆墨
1181年冬,被罷了官的辛棄疾,回到了江西上饒的帶湖新居。這裡是他幾年前就精心修建的莊園,依山傍水,景致清幽。他給莊園取名「稼軒」,自號「稼軒居士」,「稼」是種莊稼,「軒」是小屋子,意思很明白:既然報國無門,不如歸隱田園,耕讀度日。
表面上看,他好像真的放下了。詞里寫的儘是田園風光、農家樂趣:「稻花香里說豐年,聽取蛙聲一片」(《西江月·夜行黃沙道中》)。他好像很享受這種「味無味處求吾樂,材不材間過此生」的閒適。
朋友們也來了,朱熹、陳亮這些名士,在鵝湖寺、瓢泉邊,與他論道談詩。
可了解辛棄疾的人都知道,他骨子裡的火,從未熄滅。閒居,對他這種「青兕」(青黑色犀牛,喻指勇猛非凡)般的人物來說,是不得已的退讓,是錐心的痛苦。
那首看似悠閒的《鷓鴣天》里,緊接著「寧作我,豈其卿」的,就是一句沉痛的「人間走遍卻歸耕」。走遍人間路,最終卻只能回家種地,這其中的不甘與憤懣,呼之欲出。
最讓人熱血沸騰的,是他與摯友陳亮(字同甫)的「鵝湖之會」。1188年冬天,陳亮來信約辛棄疾和朱熹在鉛山紫溪商討抗金大計。
朱熹沒來,辛棄疾當時正病著,卻一直在瓢泉苦苦等待。一個雪後初晴的傍晚,他倚欄遠眺,突然看見陳亮騎著大紅馬出現在村前驛道上!辛棄疾頓時「大病若失」,策馬相迎。
兩位志同道合的朋友,佇立石橋,在夕陽餘暉中縱論天下,說到山河破碎、壯志難酬,悲憤難抑,竟拔劍斬斷馬鞍,指天盟誓:此生必為收復中原奮鬥到底!
這次會面後,辛棄疾寫下了那首氣沖霄漢的《賀新郎》,發出了震爍千古的吶喊:「男兒到死心如鐵,看試手,補天裂!」
這才是辛棄疾!歸隱的田園,關不住他補天之志;手中的筆墨,化作了他的刀槍劍戟。
於是,我們讀到了《破陣子·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》
醉里挑燈看劍,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聲。沙場秋點兵……
夢得再酣暢,醒來仍是「可憐白髮生」的空寂。
於是,我們讀到了《水龍吟·登建康賞心亭》
把吳鉤看了,欄杆拍遍,無人會,登臨意。縱有季鷹思鄉、劉備雄才的典故堆疊,最終只化作「倩何人喚取,紅巾翠袖,搵英雄淚」的蒼涼。
於是,我們讀到了晚年那首《永遇樂·京口北固亭懷古》
千古江山,英雄無覓孫仲謀處……想當年,金戈鐵馬,氣吞萬里如虎……憑誰問:廉頗老矣,尚能飯否?
這哪裡是懷古?分明是一位白髮老將,用盡生命最後的氣力,發出的泣血叩問與不甘!
他把戰場搬進了詞章,把刀劍熔進了筆墨。
豪放時,如大江奔涌,氣吞寰宇;沉鬱時,如幽谷迴響,愁結千鈞。他的詞,悲歌亦是戰歌。六百多首詞作,記錄了他一生的熱血、謀略、憤懣與堅守,成就了「詞中之龍」的千古絕唱。
千古忠魂意難平
歷史有時充滿了諷刺。當辛棄疾在江西鄉間日漸老去,南宋朝廷卻又想起了這頭暮年的「猛虎」。1203年,主張北伐的權臣韓侂胄當政,急需藉助老將的威望和經驗。
於是,64歲高齡的辛棄疾被重新起用,先是任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,緊接著又被派到抗金最前沿的鎮江做知府。
機會!遲來了近四十年的機會似乎就在眼前!老病纏身的辛棄疾,一接到任命,仿佛年輕了二十歲。他立刻投入工作:招募壯丁,整飭軍備,派遣間諜深入金國搜集情報。
他敏銳地察覺到,金國內部矛盾重重,蒙古在北方崛起,正是北伐的有利時機。
但辛棄疾畢竟是辛棄疾,他不會為了迎合主戰派而盲目樂觀。基於對宋金雙方實力的深刻了解(這經驗是用半生蹉跎換來的),他給朝廷潑了一盆「冷水」:金國未到必亡之時,南宋更需充分準備!
他憂心忡忡地指出,南宋軍隊幾十年沒打過仗,將領都是權貴子弟,缺乏實戰經驗,兵器裝備也老舊不堪,這樣倉促北伐,風險極大。
這番老成謀國之言,在狂熱的主戰派聽來,簡直是「潑冷水」、「唱反調」。再加上他剛正不阿的性格,很快又得罪了人。
僅僅一年多,辛棄疾就因一次舉薦人才的小失誤被抓住把柄,再次被彈劾罷官。他回到了鉛山瓢泉,那個他曾與陳亮斬馬盟誓的地方。
這一次離開,辛棄疾知道,自己再也回不來了。北伐果然如他所料,「開禧北伐」在短暫取得小勝後,迅速潰敗。韓侂胄被殺,南宋再次與金國屈辱議和。
消息傳到鉛山,病榻上的辛棄疾,該是怎樣的悲憤交加?1207年秋天,朝廷或許感到了愧疚,或許還想借重他的名望支撐危局,下詔任命他為樞密都承旨(軍事要職),命他速回臨安商議軍情。然而,詔書抵達鉛山時,68歲的辛棄疾已病入膏肓,根本無法赴任。
農曆九月初十(1207年10月3日),這位一生以「恢復」為志的曠世奇才,走到了生命盡頭。據《歷城縣誌》等記載,臨終之際,昏沉中的辛棄疾突然圓睜雙目,連呼三聲:「殺賊!殺賊!殺賊!」 隨後,溘然長逝。
三聲「殺賊」,耗盡了他最後的氣力,也道盡了他一生的壯志未酬和無窮遺恨。
他死後,南宋朝廷追贈少師,諡號「忠敏」。
辛棄疾的結局,實在令人扼腕。文人里最能打,年輕時萬軍之中取叛將首級如探囊取物;武將里最有文才,筆下詞章雄視千古。他本可成為衛青、霍去病那樣的曠世名將,光復河山,青史彪炳。
命運卻把他推向了最深的矛盾漩渦:一身本領,生在了一個怯戰偷安的時代;滿腔熱血,困在了一個猜忌排擠的朝堂。他用刀劍寫下的開篇如此驚艷,最終卻只能用筆墨,在悲憤與不甘中,刻下那個時代最沉重的嘆息和一個民族永不磨滅的英雄氣概。
這,或許才是他最大的「可惜」。
這膽氣、這武力值、這執行力,簡直是天神下凡!這一戰,讓辛棄疾在義軍中聲威大振,也初步顯露了他絕非僅靠筆墨吃飯的驚人一面。但這,竟然還不是他最巔峰的表演!
更大的風暴,很快就要降臨在他身上。
南歸的猛虎
帶著活捉張安國的傳奇戰績,年僅23歲的辛棄疾終於踏上了南宋的土地。這個在金人鐵蹄下長大的「歸正人」,滿腔熱血只想為故國效力,收復中原。他以為到了「自己人」的朝廷,就能大展拳腳。現實卻給了他當頭一棒。
南宋朝廷對他這樣的「北來豪傑」,態度極其矛盾。一方面欣賞他的勇猛和能力,宋高宗趙構就親自接見了他,授予他江陰簽判的官職。另一方面,朝廷上下瀰漫著對金人根深蒂固的恐懼和主和苟安的氛圍。
像辛棄疾這樣敢打敢拼、堅決主戰的人物,反而成了「不穩定因素」,處處受猜忌、排擠。
辛棄疾哪管這些彎彎繞繞?他骨子裡就是個行動派。官職不大,照樣給朝廷上書!短短几年間,他寫出了震動朝野的《美芹十論》(又稱《御戎十論》)和《九議》。
這些可不是文人空談,而是實實在在的軍事戰略。他詳細分析金國「虛胖」的本質,地盤太大管不過來,民族壓迫太重人心不穩,這正是南宋反攻的絕佳機會。
他還具體規劃了南宋該如何積蓄力量、訓練精兵、籌措軍費,甚至提出了從山東出兵直搗河朔的北伐路線圖。
道理講得透徹,方案寫得紮實,結果呢?石沉大海。
主和派當道,皇帝也沒決心,這些凝聚了他心血和智慧的策論,最終被束之高閣。辛棄疾這才有點明白了,在南宋當官,光有本事和熱血遠遠不夠。
既然中央用不上力,他就在地方上使勁!機會來了。1179年,辛棄疾調任湖南安撫使,掌管一方軍政。
當時的湖南,地處南宋邊疆,西邊和南邊連著兩廣,再往外就是少數民族聚居的溪峒地區,山賊草寇經常作亂,治安極差,軍隊也疲軟不堪。
辛棄疾一看這情況,立刻拍板:必須練一支能打的精兵!他力排眾議,要在長沙馬殷營壘的故址上,打造一支新軍,這就是後來威震南方的「飛虎軍」。
建軍的難度超乎想像。樞密院(相當於中央軍委)里就有反對派,不斷給辛棄疾使絆子,想讓他幹不成,經費更是天文數字。
有人抓住這點,直接告到皇帝那裡,說他「聚斂民財」。皇帝一聽,趕緊發下金字牌,命令工程「立刻停止」!
換成別人,可能就認栽了。但他是辛棄疾!接到金牌,他面不改色地收起來,轉頭就對工程負責人下了死命令:「一個月!飛虎軍營柵必須建成!完不成,軍法處置!」
他親自調度,精打細算,甚至遇到連月陰雨、造瓦困難時,想出了讓居民每家獻出兩塊屋檐瓦的妙招,短短兩天就湊齊了二十萬片瓦。一個月後,軍營如期建成。
辛棄疾把工程報告和圖紙呈給皇帝,條理清晰,帳目明白,皇帝這才消了氣。這支飛虎軍,後來成了「雄鎮一方」、「江上諸軍之冠」的勁旅。
但辛棄疾的「硬核」作風,也徹底得罪了朝中權貴。1181年,飛虎軍建成不久,他就被扣上「用錢如泥沙,殺人如草芥」的罪名,罷官免職。
更憋屈的還在後頭。幾年後江西鬧大饑荒,朝廷又想起辛棄疾的辦事能力,派他去賑災。他一到災區,雷厲風行:貼出告示,宣布「囤糧不賣者流放,強買搶糧者斬首」!
接著拿出官府所有錢財,發動官民中有門路的人去外地買糧,承諾不收利息,月底運回平價銷售。很快,運糧船隊絡繹不絕,糧價應聲下跌,百姓得以活命。
這時鄰近的信州(今江西上饒)也鬧饑荒,太守謝源明求援。辛棄疾的部下都反對:我們自己還不夠呢!辛棄疾卻大手一揮:「都是大宋百姓,都是皇上的子民!」 當即調撥了三分之一糧船支援信州。
皇帝為此嘉獎了他,升了一級俸祿。可沒過多久,他又被言官彈劾,再次丟官。
一次次的起用,一次次的建功,又一次次的罷免……辛棄疾這隻北歸的猛虎,縱有裂石之爪、嘯谷之威,終究被死死困在了南宋朝廷這個精緻的牢籠里。
把刀劍熔進筆墨
1181年冬,被罷了官的辛棄疾,回到了江西上饒的帶湖新居。這裡是他幾年前就精心修建的莊園,依山傍水,景致清幽。他給莊園取名「稼軒」,自號「稼軒居士」,「稼」是種莊稼,「軒」是小屋子,意思很明白:既然報國無門,不如歸隱田園,耕讀度日。
表面上看,他好像真的放下了。詞里寫的儘是田園風光、農家樂趣:「稻花香里說豐年,聽取蛙聲一片」(《西江月·夜行黃沙道中》)。他好像很享受這種「味無味處求吾樂,材不材間過此生」的閒適。
朋友們也來了,朱熹、陳亮這些名士,在鵝湖寺、瓢泉邊,與他論道談詩。
可了解辛棄疾的人都知道,他骨子裡的火,從未熄滅。閒居,對他這種「青兕」(青黑色犀牛,喻指勇猛非凡)般的人物來說,是不得已的退讓,是錐心的痛苦。
那首看似悠閒的《鷓鴣天》里,緊接著「寧作我,豈其卿」的,就是一句沉痛的「人間走遍卻歸耕」。走遍人間路,最終卻只能回家種地,這其中的不甘與憤懣,呼之欲出。
最讓人熱血沸騰的,是他與摯友陳亮(字同甫)的「鵝湖之會」。1188年冬天,陳亮來信約辛棄疾和朱熹在鉛山紫溪商討抗金大計。
朱熹沒來,辛棄疾當時正病著,卻一直在瓢泉苦苦等待。一個雪後初晴的傍晚,他倚欄遠眺,突然看見陳亮騎著大紅馬出現在村前驛道上!辛棄疾頓時「大病若失」,策馬相迎。
兩位志同道合的朋友,佇立石橋,在夕陽餘暉中縱論天下,說到山河破碎、壯志難酬,悲憤難抑,竟拔劍斬斷馬鞍,指天盟誓:此生必為收復中原奮鬥到底!
這次會面後,辛棄疾寫下了那首氣沖霄漢的《賀新郎》,發出了震爍千古的吶喊:「男兒到死心如鐵,看試手,補天裂!」
這才是辛棄疾!歸隱的田園,關不住他補天之志;手中的筆墨,化作了他的刀槍劍戟。
於是,我們讀到了《破陣子·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》
醉里挑燈看劍,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聲。沙場秋點兵……
夢得再酣暢,醒來仍是「可憐白髮生」的空寂。
於是,我們讀到了《水龍吟·登建康賞心亭》
把吳鉤看了,欄杆拍遍,無人會,登臨意。縱有季鷹思鄉、劉備雄才的典故堆疊,最終只化作「倩何人喚取,紅巾翠袖,搵英雄淚」的蒼涼。
於是,我們讀到了晚年那首《永遇樂·京口北固亭懷古》
千古江山,英雄無覓孫仲謀處……想當年,金戈鐵馬,氣吞萬里如虎……憑誰問:廉頗老矣,尚能飯否?
這哪裡是懷古?分明是一位白髮老將,用盡生命最後的氣力,發出的泣血叩問與不甘!
他把戰場搬進了詞章,把刀劍熔進了筆墨。
豪放時,如大江奔涌,氣吞寰宇;沉鬱時,如幽谷迴響,愁結千鈞。他的詞,悲歌亦是戰歌。六百多首詞作,記錄了他一生的熱血、謀略、憤懣與堅守,成就了「詞中之龍」的千古絕唱。
千古忠魂意難平
歷史有時充滿了諷刺。當辛棄疾在江西鄉間日漸老去,南宋朝廷卻又想起了這頭暮年的「猛虎」。1203年,主張北伐的權臣韓侂胄當政,急需藉助老將的威望和經驗。
於是,64歲高齡的辛棄疾被重新起用,先是任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,緊接著又被派到抗金最前沿的鎮江做知府。
機會!遲來了近四十年的機會似乎就在眼前!老病纏身的辛棄疾,一接到任命,仿佛年輕了二十歲。他立刻投入工作:招募壯丁,整飭軍備,派遣間諜深入金國搜集情報。
他敏銳地察覺到,金國內部矛盾重重,蒙古在北方崛起,正是北伐的有利時機。
但辛棄疾畢竟是辛棄疾,他不會為了迎合主戰派而盲目樂觀。基於對宋金雙方實力的深刻了解(這經驗是用半生蹉跎換來的),他給朝廷潑了一盆「冷水」:金國未到必亡之時,南宋更需充分準備!
他憂心忡忡地指出,南宋軍隊幾十年沒打過仗,將領都是權貴子弟,缺乏實戰經驗,兵器裝備也老舊不堪,這樣倉促北伐,風險極大。
這番老成謀國之言,在狂熱的主戰派聽來,簡直是「潑冷水」、「唱反調」。再加上他剛正不阿的性格,很快又得罪了人。
僅僅一年多,辛棄疾就因一次舉薦人才的小失誤被抓住把柄,再次被彈劾罷官。他回到了鉛山瓢泉,那個他曾與陳亮斬馬盟誓的地方。
這一次離開,辛棄疾知道,自己再也回不來了。北伐果然如他所料,「開禧北伐」在短暫取得小勝後,迅速潰敗。韓侂胄被殺,南宋再次與金國屈辱議和。
消息傳到鉛山,病榻上的辛棄疾,該是怎樣的悲憤交加?1207年秋天,朝廷或許感到了愧疚,或許還想借重他的名望支撐危局,下詔任命他為樞密都承旨(軍事要職),命他速回臨安商議軍情。然而,詔書抵達鉛山時,68歲的辛棄疾已病入膏肓,根本無法赴任。
農曆九月初十(1207年10月3日),這位一生以「恢復」為志的曠世奇才,走到了生命盡頭。據《歷城縣誌》等記載,臨終之際,昏沉中的辛棄疾突然圓睜雙目,連呼三聲:「殺賊!殺賊!殺賊!」 隨後,溘然長逝。
三聲「殺賊」,耗盡了他最後的氣力,也道盡了他一生的壯志未酬和無窮遺恨。
他死後,南宋朝廷追贈少師,諡號「忠敏」。
辛棄疾的結局,實在令人扼腕。文人里最能打,年輕時萬軍之中取叛將首級如探囊取物;武將里最有文才,筆下詞章雄視千古。他本可成為衛青、霍去病那樣的曠世名將,光復河山,青史彪炳。
命運卻把他推向了最深的矛盾漩渦:一身本領,生在了一個怯戰偷安的時代;滿腔熱血,困在了一個猜忌排擠的朝堂。他用刀劍寫下的開篇如此驚艷,最終卻只能用筆墨,在悲憤與不甘中,刻下那個時代最沉重的嘆息和一個民族永不磨滅的英雄氣概。
這,或許才是他最大的「可惜」。
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