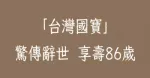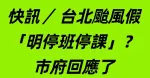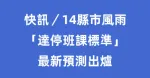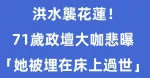1/3
下一頁
明代奇事:美婦紅杏出牆,丈夫隱忍不發,一年後娶了姦夫的結髮妻

1/3
明朝年間,蘇州府的楓橋碼頭,向來是商賈雲集之地,南來北往,好不熱鬧。
這一日,同鄉會的一場酒宴上,兩個年輕商人一見如故。一個是在此地販賣珠寶的湖廣襄陽客,自稱羅小官人;另一個是徽州來的米商,名叫陳商,也叫陳大郎。兩人年歲相仿,樣貌都頗為俊俏,幾杯酒下肚,便稱兄道弟起來。
時值五月,天氣炎熱。席間,兩人敞開衣襟飲酒,陳商身上露出的一件內衫,卻讓那羅小官人心中猛地一驚。
那是一件用細小珍珠串成的衫子,在燭光下流光溢彩,正是他蔣家祖傳的寶貝,名曰「珍珠衫」。此物冬暖夏涼,他臨行前親手交予妻子王三巧貼身收藏,怎會穿在一個外人身上?
羅小官人不動聲色,只誇讚此衫精美罕見。陳商幾分醉意,又自恃與他投緣,便得意地問道:「羅兄可認得貴縣大市街的蔣興哥?」
這羅小官人,正是蔣興哥本人。他為方便行商,一直用的是母姓。此刻聽陳商提起自己,他心頭一沉,只推說:「聽過此人,但未深交。陳兄何故問起?」
陳商壓低聲音,面帶炫耀之色,竟將自己如何與蔣興哥的妻子三巧兒相好,如何私通半年,又是何等恩愛纏綿,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。說完,還拉著身上的珍珠衫,眼淚汪汪道:「此衫便是他渾家所贈,以表情意。我此次回鄉,還托羅兄捎一封信與她。」
蔣興哥聽罷,只覺得五雷轟頂,腹中如針刺刀絞一般。他強忍怒火,口中連聲答應,心裡卻已翻江倒海。
他想不通,自己與妻子王三巧成婚四年,恩愛非常,只因生意才分別一年有餘。臨走時,妻子還指著院中椿樹,約定樹發芽時便盼他歸來。這般情深義重,怎會生出這等醜事?
這珍珠衫是鐵證,由不得他不信。
當下,蔣興哥推說不勝酒力,急急起身告辭。回到客店,他一夜無眠。第二日天還未亮,他便收拾行囊,催促船家即刻返航。
剛要離岸,陳商氣喘吁吁地追來,將一個包裹塞到他手中,千叮萬囑,務必送到大市街東巷的薛婆家轉交。蔣興哥面如死灰,接過包裹,待陳商走後,他當即拆開。
裡面是一條桃紅色的縐紗汗巾,還有一個紙匣,裝著一根羊脂玉的鳳頭簪。信中言語輕佻,只說是送與「心愛娘子三巧兒」的信物。
蔣興哥怒不可遏,將信撕得粉碎,丟入河中。又舉起玉簪,猛地在船板上折為兩段。可轉念一想,他又將這斷簪和汗巾撿起,收了起來。
他要留著這個證物。
船行如飛,蔣興哥歸心似箭,可越是臨近家門,他的心就越是沉重。進了家門,夫妻相見,他一言不發。王三巧自知有愧,滿面羞慚,也不敢上前多話。
次日一早,蔣興哥對三巧兒說:「岳父岳母同時病重,危在旦夕,你速速回去探望。我已備好轎子在門口。」
三巧兒信以為真,慌忙將家中箱籠鑰匙交予丈夫,便跟著一個婆子乘轎而去。蔣興哥隨即叫住那婆子,從袖中取出一封信,讓她轉交王公,並言明讓她送完信便可回家,不必再回蔣家。
王三巧回到娘家,見父母安然無恙,頓時大驚失色。王公從婆子手中接過信,拆開一看,竟是一紙休書。書中並未點破姦情,只說妻子有過,按「七出之條」休棄,並附上了那條桃紅汗巾與那根斷成兩截的玉簪。
王公又驚又怒,當即趕到蔣家質問。蔣興哥不願將家醜外揚,只冷冷說道:「岳父大人,家傳的珍珠衫一件,是令愛貼身收藏的,只問她如今還在不在。若在,休書之事便罷;若不在,也休怪小婿無情。」
王公回家追問女兒,三巧兒聽聞「珍珠衫」三字,頓時面如白紙,一句話也說不出,只是號啕大哭。真相至此,已無需多言。
蔣興哥休妻之後,又將家中兩個丫鬟捆了拷問。二婢吃打不過,便將如何被薛婆收買,如何為陳商與主母通風報信、開門引路的事全盤托出。
原來,竟是一個叫薛婆的牙婆從中牽線。
第二日,蔣興哥帶了家丁,直奔薛婆家中。薛婆自知理虧,躲藏不出。蔣興哥也不與她廢話,命人將其家宅打毀,出了一口惡氣。隨後,又將那兩個不忠的丫鬟轉賣了出去。
事情辦完,蔣興哥卻並未覺得快意。他看著滿屋的箱籠嫁妝,都是與三巧兒恩愛時的見證,如今物是人非,不忍再看,便叫人將十六隻箱籠盡數用封條打叉封存,原封不動地放在樓上。
光陰流轉,不久後,南京新科進士吳傑赴任廣東潮陽知縣,途經襄陽。吳知縣尚未娶妻,聽聞王公之女美貌,便遣媒說親,願出五十金聘為妾室。王公應允,蔣興哥聽聞後也並無阻攔。
三巧兒出嫁之夜,蔣興哥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。他雇了人手,將樓上那十六隻封存的箱籠,連同鑰匙,一併抬到了吳知縣的船上,贈予前妻做了嫁妝。
此事過後,蔣興哥心灰意冷,無心續弦。直到一年後,才經人說合,娶了一位新婦。這婦人姓平,也是徽州人氏,據說是隨丈夫陳客來襄陽經商,不料丈夫客死他鄉,她賣身葬夫,為人賢良。
蔣興哥見她舉止端莊,很是敬重,夫妻二人倒也和睦。
碰巧有一日,平氏在房中整理亡夫遺物,取出一件衣衫。蔣興哥只看了一眼,便呆立當場。
那正是一件珍珠衫。
這一日,同鄉會的一場酒宴上,兩個年輕商人一見如故。一個是在此地販賣珠寶的湖廣襄陽客,自稱羅小官人;另一個是徽州來的米商,名叫陳商,也叫陳大郎。兩人年歲相仿,樣貌都頗為俊俏,幾杯酒下肚,便稱兄道弟起來。
時值五月,天氣炎熱。席間,兩人敞開衣襟飲酒,陳商身上露出的一件內衫,卻讓那羅小官人心中猛地一驚。
那是一件用細小珍珠串成的衫子,在燭光下流光溢彩,正是他蔣家祖傳的寶貝,名曰「珍珠衫」。此物冬暖夏涼,他臨行前親手交予妻子王三巧貼身收藏,怎會穿在一個外人身上?
羅小官人不動聲色,只誇讚此衫精美罕見。陳商幾分醉意,又自恃與他投緣,便得意地問道:「羅兄可認得貴縣大市街的蔣興哥?」
這羅小官人,正是蔣興哥本人。他為方便行商,一直用的是母姓。此刻聽陳商提起自己,他心頭一沉,只推說:「聽過此人,但未深交。陳兄何故問起?」
陳商壓低聲音,面帶炫耀之色,竟將自己如何與蔣興哥的妻子三巧兒相好,如何私通半年,又是何等恩愛纏綿,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。說完,還拉著身上的珍珠衫,眼淚汪汪道:「此衫便是他渾家所贈,以表情意。我此次回鄉,還托羅兄捎一封信與她。」
蔣興哥聽罷,只覺得五雷轟頂,腹中如針刺刀絞一般。他強忍怒火,口中連聲答應,心裡卻已翻江倒海。
他想不通,自己與妻子王三巧成婚四年,恩愛非常,只因生意才分別一年有餘。臨走時,妻子還指著院中椿樹,約定樹發芽時便盼他歸來。這般情深義重,怎會生出這等醜事?
這珍珠衫是鐵證,由不得他不信。
當下,蔣興哥推說不勝酒力,急急起身告辭。回到客店,他一夜無眠。第二日天還未亮,他便收拾行囊,催促船家即刻返航。
剛要離岸,陳商氣喘吁吁地追來,將一個包裹塞到他手中,千叮萬囑,務必送到大市街東巷的薛婆家轉交。蔣興哥面如死灰,接過包裹,待陳商走後,他當即拆開。
裡面是一條桃紅色的縐紗汗巾,還有一個紙匣,裝著一根羊脂玉的鳳頭簪。信中言語輕佻,只說是送與「心愛娘子三巧兒」的信物。
蔣興哥怒不可遏,將信撕得粉碎,丟入河中。又舉起玉簪,猛地在船板上折為兩段。可轉念一想,他又將這斷簪和汗巾撿起,收了起來。
他要留著這個證物。
船行如飛,蔣興哥歸心似箭,可越是臨近家門,他的心就越是沉重。進了家門,夫妻相見,他一言不發。王三巧自知有愧,滿面羞慚,也不敢上前多話。
次日一早,蔣興哥對三巧兒說:「岳父岳母同時病重,危在旦夕,你速速回去探望。我已備好轎子在門口。」
三巧兒信以為真,慌忙將家中箱籠鑰匙交予丈夫,便跟著一個婆子乘轎而去。蔣興哥隨即叫住那婆子,從袖中取出一封信,讓她轉交王公,並言明讓她送完信便可回家,不必再回蔣家。
王三巧回到娘家,見父母安然無恙,頓時大驚失色。王公從婆子手中接過信,拆開一看,竟是一紙休書。書中並未點破姦情,只說妻子有過,按「七出之條」休棄,並附上了那條桃紅汗巾與那根斷成兩截的玉簪。
王公又驚又怒,當即趕到蔣家質問。蔣興哥不願將家醜外揚,只冷冷說道:「岳父大人,家傳的珍珠衫一件,是令愛貼身收藏的,只問她如今還在不在。若在,休書之事便罷;若不在,也休怪小婿無情。」
王公回家追問女兒,三巧兒聽聞「珍珠衫」三字,頓時面如白紙,一句話也說不出,只是號啕大哭。真相至此,已無需多言。
蔣興哥休妻之後,又將家中兩個丫鬟捆了拷問。二婢吃打不過,便將如何被薛婆收買,如何為陳商與主母通風報信、開門引路的事全盤托出。
原來,竟是一個叫薛婆的牙婆從中牽線。
第二日,蔣興哥帶了家丁,直奔薛婆家中。薛婆自知理虧,躲藏不出。蔣興哥也不與她廢話,命人將其家宅打毀,出了一口惡氣。隨後,又將那兩個不忠的丫鬟轉賣了出去。
事情辦完,蔣興哥卻並未覺得快意。他看著滿屋的箱籠嫁妝,都是與三巧兒恩愛時的見證,如今物是人非,不忍再看,便叫人將十六隻箱籠盡數用封條打叉封存,原封不動地放在樓上。
光陰流轉,不久後,南京新科進士吳傑赴任廣東潮陽知縣,途經襄陽。吳知縣尚未娶妻,聽聞王公之女美貌,便遣媒說親,願出五十金聘為妾室。王公應允,蔣興哥聽聞後也並無阻攔。
三巧兒出嫁之夜,蔣興哥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。他雇了人手,將樓上那十六隻封存的箱籠,連同鑰匙,一併抬到了吳知縣的船上,贈予前妻做了嫁妝。
此事過後,蔣興哥心灰意冷,無心續弦。直到一年後,才經人說合,娶了一位新婦。這婦人姓平,也是徽州人氏,據說是隨丈夫陳客來襄陽經商,不料丈夫客死他鄉,她賣身葬夫,為人賢良。
蔣興哥見她舉止端莊,很是敬重,夫妻二人倒也和睦。
碰巧有一日,平氏在房中整理亡夫遺物,取出一件衣衫。蔣興哥只看了一眼,便呆立當場。
那正是一件珍珠衫。
 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