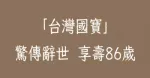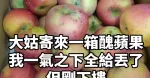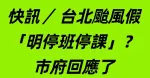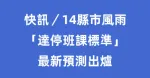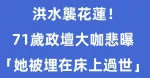2/4
下一頁
妻子19歲早逝,他跪在棺木前3天3夜,之後對岳父發誓:終身不再娶

2/4
婚後分別
1988年,婚禮那日,馬一浮眉宇間尚存幾分羞澀,卻難掩眼底的驚艷;而湯儀低垂眼帘,嬌羞含笑。
可惜,良辰美景總難久駐,成婚未滿月,湯家忽然傳來家書,告知父親生病。
而此前早已定下,馬一浮需啟程赴上海繼續求學,備戰科舉之外,還需參與新辦的《翻譯世界》月刊,推動新思潮的傳播。
馬一浮知曉,身為人子,此刻更應擔起肩頭責任;可也是在此刻,他第一次真正明白,原來離別,竟是這般刺痛。
湯儀並未阻攔,她為他整好行囊,在他懷中塞了一包她親手縫製的布鞋,又把繡著蘭花的帕子放進了他的衣襟口袋。
別後,一封封書信成了他們唯一的聯結,湯儀每日清晨抄書,夜裡寫信。
她在信中細數家中瑣事,講鄰里新事,也談自己的讀書心得。
而馬一浮的回信則更多是鼓勵與勸勉,他勸她多讀書,莫荒廢時光。
更大的打擊,在1901年驟然降臨。
馬廷培病逝,馬一浮匆匆返鄉,履行為人子應盡的守孝之禮。
那一日,馬家掛滿白幡,湯儀站在靈前,默默扶持著丈夫操持一切。
但命運未曾憐惜他們的堅忍,就在馬家喪事未畢之際,湯儀察覺身體有異。
診脈之下,喜脈已現,她未曾歡喜太久,便被當地的風俗繩索束縛住了雙手。
守孝期間若生子,乃不祥之兆,會被族中視為不敬、不忠,甚至可能為家族帶來「天譴」。
馬一浮不信那些陳腐禮教,可他身在其中,又怎能輕易掙脫?他不舍湯儀受苦,更不願孩子無辜而亡。
而那晚,湯儀主動端來茶水說:「此子與我有緣卻無命,你我還年輕,將來定會有子嗣。」
可流產之後,湯儀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,原本紅潤的臉頰逐漸消瘦,走幾步便氣喘吁吁。
而她依舊隱忍不言,每每寫信給馬一浮,仍舊報喜不報憂,她從未說自己幾次因虛弱暈倒,也未告訴他自己有多怕夜裡一個人咳得喘不過氣。
隻字未提那日流產後的劇痛如何蝕骨蝕心,她只想留給丈夫最安心的訊息,不讓他在遠方為她分心一分一毫。
但紙終究包不住火,1902年的一天,馬一浮收到岳父急電:儀兒病危,速歸!
1988年,婚禮那日,馬一浮眉宇間尚存幾分羞澀,卻難掩眼底的驚艷;而湯儀低垂眼帘,嬌羞含笑。
可惜,良辰美景總難久駐,成婚未滿月,湯家忽然傳來家書,告知父親生病。
而此前早已定下,馬一浮需啟程赴上海繼續求學,備戰科舉之外,還需參與新辦的《翻譯世界》月刊,推動新思潮的傳播。
馬一浮知曉,身為人子,此刻更應擔起肩頭責任;可也是在此刻,他第一次真正明白,原來離別,竟是這般刺痛。
湯儀並未阻攔,她為他整好行囊,在他懷中塞了一包她親手縫製的布鞋,又把繡著蘭花的帕子放進了他的衣襟口袋。
別後,一封封書信成了他們唯一的聯結,湯儀每日清晨抄書,夜裡寫信。
她在信中細數家中瑣事,講鄰里新事,也談自己的讀書心得。
而馬一浮的回信則更多是鼓勵與勸勉,他勸她多讀書,莫荒廢時光。
更大的打擊,在1901年驟然降臨。
馬廷培病逝,馬一浮匆匆返鄉,履行為人子應盡的守孝之禮。
那一日,馬家掛滿白幡,湯儀站在靈前,默默扶持著丈夫操持一切。
但命運未曾憐惜他們的堅忍,就在馬家喪事未畢之際,湯儀察覺身體有異。
診脈之下,喜脈已現,她未曾歡喜太久,便被當地的風俗繩索束縛住了雙手。
守孝期間若生子,乃不祥之兆,會被族中視為不敬、不忠,甚至可能為家族帶來「天譴」。
馬一浮不信那些陳腐禮教,可他身在其中,又怎能輕易掙脫?他不舍湯儀受苦,更不願孩子無辜而亡。
而那晚,湯儀主動端來茶水說:「此子與我有緣卻無命,你我還年輕,將來定會有子嗣。」
可流產之後,湯儀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,原本紅潤的臉頰逐漸消瘦,走幾步便氣喘吁吁。
而她依舊隱忍不言,每每寫信給馬一浮,仍舊報喜不報憂,她從未說自己幾次因虛弱暈倒,也未告訴他自己有多怕夜裡一個人咳得喘不過氣。
隻字未提那日流產後的劇痛如何蝕骨蝕心,她只想留給丈夫最安心的訊息,不讓他在遠方為她分心一分一毫。
但紙終究包不住火,1902年的一天,馬一浮收到岳父急電:儀兒病危,速歸!
 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